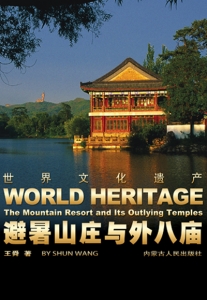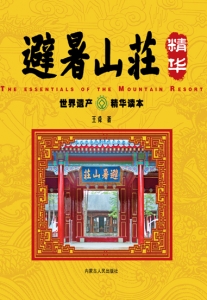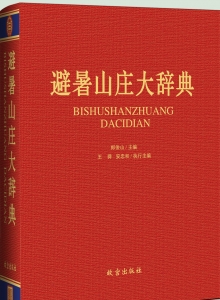《九江诗话》 步九江 著

九 江 写 意

九 江 写 意
——读《九江四味集》
田 林
九江是一个人。不是九条江或是叫作九江的一条江。九江姓步,出了一本诗集——《九江四味集》。
然说到九江,绝无捧意。我也是个业余作者,只是说点儿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点滴真话。读书,更是读人。九江写了这么多年诗,还真弄出点儿“名堂”来。(看官:一个人一生若能写出一两首传世之作,也就算对得起自己啦。)这里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,但并非传世之作:
《冷艳》:在北方,/谁说春来晚?/北方的温度计,/是透明的血管。/“三九”天的水银柱,/有着盛暑的情感,/……/北方的春,/横向联合最远!/只要读懂大雁的翅膀——/便可以和任何地方交换。
《今年的气候格外好》:你闻闻那喷香的泥土,/你摸摸那烫手的新犁,/哥嫂的对话被豆芽听见,/她一使劲钻出了地皮。
《村头的路》:阳坡的古松阴坡的藤,/藤搂着松——仰面不见天!/那时不知什么叫作“走”,/出门习惯用语都说“钻”。/旧社会长腿有啥用?/多一层仇苦:走——路——难。
九江的诗不矫情,全是大实话。然而把大实话变成诗是不容易的。听着顺耳,品着有味儿,你说这是个多么高的艺术水准?我不想去解释他的诗,只需大家来品,品出味道来,哑然一笑,品不出是自己的事儿。不矫情的别一种说法便是朴实。朴实是一种境界,是返朴归真,是否定之否定后的艺术升华。依我看能把诗写到真正的“朴实”份儿上是和九江的性格有关,创作上便是风格。该君就是个朴实主义。电视台的同志们给九江这样几句话:衣着象村长,一副热心肠,喝酒不知醉,闲话唠半晌。他是真正的乐于助人,在他眼里,大家都很不容易,常常是让人觉得他是怀着一种对人生感悟的同情心在与你共事。同情心,善良、正义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呵。总之,“村长”是好人。朴实。他总是那么匆匆忙忙的,那么忙,还写诗。有意思。
九江的诗,写得灵秀。憨憨的九江,能写出如此灵秀的诗,有点让人忍俊不禁:《忙二叔》:追星星,赶太阳,/春酿绿,/秋酿黄。/我二叔——/整天这么忙。/丢过手表,没丢过时间,/……“准确的钟点在我心上”。《遗墨当歌》:你俩虽然已走四年,/却好象离别四天,/亲人——在想,/战友——在盼。/心急火燎听列车长鸣,/——恨无处去接站!
就这么几句,请君慢慢品。他也许是偶得,也许是长期思考的结晶。现代诗讲哲理,讲感觉,讲痛苦,讲无奈,讲生命意识死亡意识……九江的诗中全有。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。他把人生的乐章奏得异常丰富。望着他的背影,我常想,九江这硕大的头颅里究竟装了多少人生的感受。他是多侧面的,多棱角的,毫不事故的,象一块干姜,越嚼越有味;有时,一点小事拍案而起;有时,天塌下来不着急。然而他的诗却写的那么灵秀、深刻。这也许该归结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隆化那片水土吧。隆化水土不错,出诗人。把诗写得既灵秀又深刻,不容易,就如同一俱,能够做到既精明又实在,不容易。灵秀往往使之轻浮,深刻往往使之枯涩,精明往往使之尖滑,实在又往往使之愚笨。作诗、作人,真是门学问。九江的名字和人结合在一起,总会使人充满幻想地演绎出他是一个由九条江汇在一起的人——复杂而又温柔,在塞北阔大的土地上缓缓流淌着。再赏:《某同志在一次会上的发言》:谁说我搞不正之风?/请君察几时吹倒过酒盅!/说实在的,为了密切“同志关系”,/狂饮也当受奖立功!/新时代的工作方法,/讲究实在就不能“假正经”。
《田野里的对话》:鞭子:假如我不抽打耕牛,/就丢掉了祖宗的传统。/我为了永久的生存,/必须把“残忍”视为光荣。/耕牛:打吧,打吧!/我从不喊疼。/因为你的躯体,/是用我长辈的牛皮拧成!/将来我也会抽打我的子孙,/只要它们总在田野上蠕动。
九江敢讲真话,胆子大!语言尖刻且有点黑色幽默中带着斜巴气儿。斜巴气,是说它怪,有特点,与众不同。这一点,在《九江活页》上,应更具气势。这里不提。
不谈空泛的审美视觉。也不谈空泛的艺术特色。只是举了几个不充分的诗例(有的甚或是1980年写的),顺便说说九江其人。为什么?因为诗是由人写出来的,写对人的认识比较圆滑,不易引起争论,若单独谈诗,便见仁见智了。不知九江读后能否接受,更不知不熟识的读者和左左右右的朋友们能否苟同。
《承德日报》1996年10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