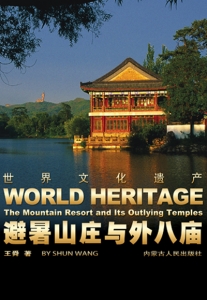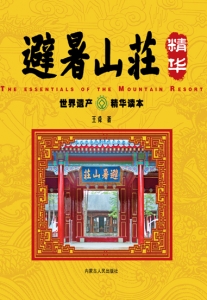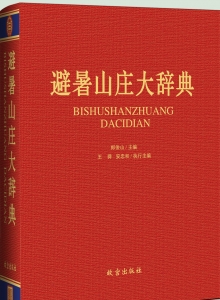山庄荷缘蕴藉在 诗词影画品性真
——浅淡李海健诗词摄影集《山庄荷缘》的人文生态美
薛 梅
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。如果是源于同一个作者的不同艺术创造,那么所流露出来的心相必然是合一的。如果借用古代艺语中“诗是有声画,画是无声诗”,那么摄影所呈现的影画也必是无声之诗,所与之唱和之诗则必是有声画了。品赏海健的诗词摄影集《山庄荷缘》,我们找到了这种契合,并为之怦然心动。海健通过诗意影画,从审美的高度出发,将现代摄影与传统诗词融熔合一,以精致的艺术形式、语言展示他对自然的感受与体验,以优雅的气息、品格体现他对艺术的追求和认识,并把这一切倾注、定位于“山庄荷花”这一独特意象,在静谧、清新与恬淡中蕴藉着他的乡土情怀、生态意识和人文精神。
海健是我的师兄,我在总论海健诗歌的人生取向时,借用了荷尔德林《返乡——致亲人》中的诗句“你梦寐以求的近在迟尺”作为总题,来详细论述海健诗歌创作的乡土情怀和人格追求。应该说海健的艺术选择是纯粹的,是严谨的,是高格调的,是纯精神的。特别是在通览他的8部现代诗集《爱之魂》、《银杏叶》、《记忆的村庄》、《星星河》、《石榴树》、《读一读承德诗人》、《香椿树》、《李海健诗选》、1部报告文学集《热土情》、1部杂文集《燕山铃语》之后,再来细品这第11部即将出版的诗词摄影集《山庄荷缘》,我们会发现一颗热爱真与美的心灵,是有着怎样坚执的求索与创造,怎样返璞归真的大境与彻悟。文心缘自然,品性留本真,他不必仰望,尊敬自在,他不必喧哗,隽永自在。
一
乡土情怀是海健一以贯之的根,体现在《山庄荷缘》的自然美上。海健不是承德人,他的童年是在冀中大平原衡水乡间度过的。然而,他1986年大学毕业后即留承工作至今,且成为承德名副其实的女婿、诗人和国家干部已经近三十年了。他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,他深谙故乡二字对于一个人、乃至人类的深重意味,“心安之处即故乡”,他安顿他的心灵,固守他的心灵,从平原到山区,从山区到平原,故乡深深扎根在乡土之中,一人一事,一物一景,无一不是触动他情感的源泉,无一不是他诗绪扎根的土壤,他的父母亲人、村庄故事都在他的笔下相伴相生,他的文朋诗友、承德风物都在他的笔下相携相行。他的宅心仁厚带给他生活的美满,他的勤于笔耕带给他精神的富足。无疑,海健的这本《山庄荷缘》正是他的有为之处,一颗种子无论落在哪里,都要此心安处,做好大地的植物,自然而不乏努力,简单而不乏智慧,汲取足够的阳光和水分,活出精彩,活出自己。
承德作为海健第二故乡,他情有独钟山庄的荷花。他对于荷花的爱到细处和深度,远不仅仅体现在影画和诗词的相互酬唱,还有他在《后记》里体现出来的不辞辛苦、细致入微的关于荷花文化的观察和体悟,他写道:“避暑山庄的荷花晚开晚谢的习性除了和品种有关以外,还和避暑山庄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”,从山庄荷花品种的来源、形状、色泽、习性、培育,到品相的艺术姿态、理想寄寓,使热爱潜隐其中,使情怀潜隐其中,自然真切,朴实可信。
二
山庄荷花的自然之美,正是海健的乡土根性使然。海健眼中笔底的荷花,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“全美”。我们知道,在传统审美观中,自然作为鉴赏对象常常被人为的打上美与丑的标记,人们常常以主观判定的审美属性作为一种身份标签,而将一部分视为“丑”的东西摒弃在外,这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局限而已。海健通过他的眼和他的心,肯定了自然的存在之美,他认同全部自然都是美的。他的文字与他的画意,相辅相成,时有机杼,特别是品赏到一幅出魂的诗句和影画完美结合到极致时,有时会心微笑,有时捧腹开怀。海健诗画不仅留下荷花不同的美的姿态,那些含苞欲滴的,碧绿河水与荷叶托出的一抹娇嫩,“两片绿叶争相望,心潮涨春一脸痴”,一“争”一“痴”,活脱脱将小女儿迷人情态写活了;那些灿然开放的,“朱腮粉唇情丝动”、“婆娑舞姿赛仙风”,那么自我,那么清丽,那么高傲,那么纯粹,一切皆缘于“闲来水边听蛙声”的相惜相引;那些成熟灼热的,“彩霞起于绿波间,透明思绪如诗篇”、“云高气爽比汉唐,玉靥妖媚沁腑香”,原来绚烂之极,正是才情使然;那些宁馨安谧的,“诗仙太白居高处”,“满池暗香挡不住”,如月如云,又如仙如境;那些老态龙钟的,“自知不招蜂蝶恋,退隐镜湖作闲人”,“已明东阁西窗事,万事一笑一身轻”。一颦一笑间,一叶一枝上,他将动与静,明与暗,深与浅,显与隐,都熔铸其间。真,历万变不离其宗;美,经万古不弃其心。海健诗画还留下了一些荷上的风流韵事,他细致捕捉到了一只蜾蠃“瞬间窃蕊即飞离”的行径,他调侃道:“好像寻花问柳人”;他以宅心仁厚的宽怀去拥抱那些残荷冷雪、那些枯梗败叶,他在凋零里发掘着衰败之美,他在沉默里积蓄着重生的祝福,“莫怕哀姿夕阳晚,坚信藕根孕新生”;海健以自然之眼看待自然,自然必以自然之美回报诗情,海健说他是幸运的,他拍到了一组山庄松枝上跃然而上的鸬鹚,这些本应在船头渔猎之物,却飞跃夏季松枝之上,“步调一致头朝东”,读来心酸又心痛。这些别有意趣之美,在海健影画中生动着,在海健文字里活脱着,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审美。海健在这些以荷花为主体意象的山庄山水风景图中,在远近、浓淡、高低之间,透露出自然存在的天堂般的和谐之美,共享着自然界万物繁衍自恰的生机。
三
生态意识是海健对传统美学的继承,体现在《山庄荷缘》的美学观照上。生态一词,尽管从词汇学角度讲,是来源于古希腊字,原意是家、居住地或我们的环境。简单的说,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,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。但生态意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,它不仅仅存在于抽象的哲学中,也保存在具象的美学中,在道家、儒家、佛家美学中都有诸多表现。并且古代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始终以一种敬畏、爱戴和欣赏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生活,将自然看得高于人类。自然是最高的美学原则。应该说,海健勇于继承这种具有博大胸怀、仁厚之心的生态意识,它不仅多年来坚持用文字建设真诚的情感家园、和谐的生态环境,近年来更通过摄影镜头来达成他的生态理念,他不仅呈现了自然界自然存在的审美价值,他更注重表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状态,他的图文景观里有他的参与性和他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,有他在与山庄、与荷花、与其他事物关联中获得的生命共感和欢歌。
从集子的总题来说,“山庄荷缘”一个“缘”字,已然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人与山庄、与山庄之荷,不再标榜人是自然的主人,而是认同自然是我们的天堂,我们是自然界中的一员,我们是身在其中共享的一员。海健镜头中每一处成像,我们都能够穿透镜头之外,看到海健跋涉、蹲伏、登高的身影,在俯仰之间,动静之间所奉献出来的一颗拳拳之心,而后进一步凝注成为诗意的文本。“我的‘山庄荷韵’主要以拍摄敖汉莲、白洋淀引种莲、武汉引种莲为主,‘山庄莲香’主要以拍摄睡莲为主,‘山庄蜓美’主要以拍摄山庄荷塘边的蜻蜓为主,‘山庄荷缘’主要以拍摄山庄荷塘边的飞物和其他花类为主。因其有塘中的荷花、塘边的蜻蜓和岸边松树上的鱼鹰,故此书名叫‘山庄荷缘’。”(《后记》)
因为这“缘”,海健在“山庄荷韵”中共鸣了“一片荷灯照乾坤”的带有暖意的清矍之美,在“山庄莲香”中共鸣了睡莲“莫道浮萍无情物,痴心一片话短长”的净心静守之美。这“缘”更将人从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,人道的善待自然,这集中体现在“山庄蜓美”和“山庄荷缘”两辑中。“山庄蜓美”是山庄蜻蜓和荷花的“复调”呈现,具有双重叙事的意味。作为荷花主核心意象,在这一辑中成为蜻蜓聚焦镜头中的一个陪衬,虚化为背景,同时,也是荷花意象的进一步伸展和完善,使荷之“隐君子”之品相更具风骨和魅力。
海健眼中的蜻蜓,是原生态的美。我们知道,蜻蜓被称为昆虫王国中不折不扣的杀手。它是不完全的变态动物,一生经历卵、稚虫和成虫三个变态期,它的生长具有史诗般的演变与轮回,也可谓是历尽千难万险才最终拥有一副可以轻盈飞翔的美丽翅膀。我们小时候常常一见蜻蜓飞过,就会一边追逐一边哼唱:“蜻蜓蜻蜓飞,底下有人追;蜻蜓蜻蜓落,底下有好贺儿”。而今这样的追逐歌唱的场景已很难见到了,生态的每况愈下已难掩其责,同时也道出了蜻蜓所有的捕杀行为皆出于后代繁衍生息,这也是它们不能回避的战斗。海健的生态意识在红色的,蓝色的,金色的,闪着各种色泽的蜻蜓中蕴藉着美,蕴藉着生生不息的挣扎和不离不弃的坚守,那些嬉戏玩耍的,那些劳碌奔忙的,那些独自彷徨的,那些悠然自得的,在荷叶上,在莲瓣上,在蕊黄里,在苇尖上,在草叶中,在断梗之上,都揭示了一种生物间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。而海健或在高处审视,或在低处动容,他都将自己熔铸其间,情蕴其中,他为蜻蜓大声宣告:“抱定绿苇不放松,今生今世与君同”。“山庄荷缘”中那些荷花上的蜜蜂、蝴蝶、肥蛾、黑衣娘、老蝈,湖中的野鸭、鱼群、鸬鹚,湖边的芍药、野菊、喇叭花、月季花,都是海健尊重和善待自然界其他成员生存、发展权力的体现,他以诗画相和来抒写她们的生态美。相对于自然美学,生态美学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关系,在本质意义上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。
四
人文精神是海健不息的创作动力,体现在《山庄荷缘》的艺术旨归上。世间大凡有品位的人,虽各有不同的境界,但有一点是共通的,那就是拒绝庸俗,崇尚创造。海健的这本诗词摄影集《山庄荷缘》,正是海健对于荷花这一传统题材匠心独运的艺术创新的重要成果,充分显示了海健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,对于当代艺术理念的深刻领会,可是说是诗画结集中出手不凡的精品。
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人学。始终贯穿着关注人、重视人、崇尚人的人文精神。中国传统美学也始终立足于人,并最终指向人的精神发展和人生活的意义。特别是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以人为本、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,也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。而这种深深镌刻着中国文化内在基因的花卉艺术意象比比皆是,富贵大方的牡丹,傲霜斗寒的秋菊,馨香馥郁的桂花,优雅素洁的兰花,高洁忠贞的梅花,清新优雅的荷花等等。但荷花向来被称为“花中君子”而备受尊崇,它的姿态和风骨使其成为中国文人雅士心目中的自然楷模。而且从艺术层面来看,荷花也确实比一般花卉更具美感,无论是花、叶和蕾,都妙不可言。
荷花,自古雅名繁多,有芙蓉(《离骚》)、泽芝(《古今注》)、芙蕖(《尔雅·释草》)、水芝(《本草经》)、水芸(《群芳谱》)、凌波仙子和君子花(《爱莲说》)等称法,同属于睡莲科,系多年生宿根性水生草木,花叶由地下茎之节部生出。中国人对荷的认识非常早,《尔雅·释草》记载:“荷,芙蕖;其茎茄,其叶蓬,其本蓄,其华菌蔷,其实莲,其根藕,其中药,药中惹”,详细列出了荷花不同部位的不同名称。魏时的《齐民要术》记载了农业的“种藕法”,反映了古时荷花的栽培技术。到了清代出版了荷花盆栽专著《砙荷谱》,对荷花品种做了详细记录和分类。关于荷的更多优点特质的认知,影响较大的是李渔的《闲情偶记》和明代医书《本草纲目》。
荷花意象在文学领域中作为花卉意象独特的表现题材,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《诗经》时期。后来,不仅诗歌,还有文学其它题材、建筑、绘画、文学艺术研究等多种领域广泛应用。由于中国传统美学更多注重的不是对象的实体,而是功能,而“天地之性,人为贵”的人本思想,通过借景抒情、寓景于情、以及情景交融等方式表达个人的心境和情感,便使荷花具有了人在生活中所体会到的某种感情,某种精神性情的代表。从3000多年前的《诗经》到今天,荷花意象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已经走过了三千年的历程,特别是当屈原将“荷衣”披挂在他想象的完美人格之上时,荷花意象便有了非凡的转折意义和新的意蕴象征:人格审美。唐代“诗仙”李白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概括了文人雅士以荷花来形容自我的真性情;宋代杨万里的一句“学诗应透脱,信手自孤高”则将荷花的人格审美有了新的突破,即不入俗流、豁然大度、又不束于外在规矩和条例的“透脱”,更注重的是荷花意象的独立和不屈,荷花意象的人格意义便又补充了与世独立、不入俗流的君子人格精神。尽管荷花意象在后来的发展和研究、表达和寄寓中,由于它的民俗特征、地域文化、民俗习惯的独特形态,它与中国哲学思想、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的息息相关,它的爱情意蕴,它的仙化色彩,它的禅修映现,它的儒家人格和民族心性,从而具有了更加广阔和无限的丰富性,但其根本仍指人内心返璞归真,表达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处事原则。
显然,海健是深受中国传统荷花文化的濡染,他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继承了这一荷花主题,用自己的眼睛拍摄下属于自己的山庄荷花情韵,书写出自己的生命理解,其内蕴着海健非常可贵的个人品性和人文精神。我们从海健的《山庄荷缘》中窥到了这种返璞归真的人文特质。他不从众,以本心观荷,用情真,用意切,他的镜头忠实记录着荷花生长过程中的不同表现,艺术旨归上正是对生命历程的敬畏和尊崇。他在荷花细节的处理中注重大气的绿色生命底色,他在荷花独立的人格支撑里注重与万象的生命相守,他在荷花平静安谧中注重内蕴情热的生命真相。真性情中透出高贵和纯净,素朴中又包孕出昂然之美和芬芳之气,流动在影画和文字之间,宛若琴瑟相和,叮叮淙淙,濯洗我们在这个当下浮世躁动和欲望的蒙尘之心,静坐静赏,净目净心:“不管身后多少事,洗心脱尘到秋黄”。
总之,海健自觉与有意地规避和远离着唯美的肤浅和真实的简单化,他在荷花意象这一传统题材中,追求一种新的感觉、新的语境和新的意义,以寄托一个现代文人的情思与胸怀。
2013年11月17日 于承德魁福园